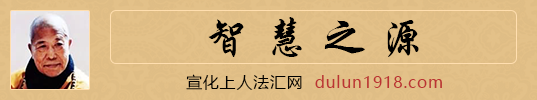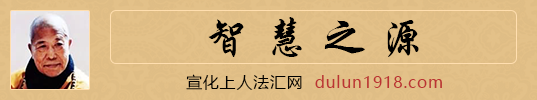◎米特可芙夫人二○○四年在教会中讲词
/孙丽钰 中译
我儿克里斯多夫.克劳里(即上恒下实法师)拜学中文之赐,有缘成为一名佛教徒。德维比斯高中毕业的他,在顺利拿到奥克兰大学学士学位后,成为柏克莱加州大学的「丹佛人」(丹佛奖学金得主)。在柏克莱,他以翻译佛经来作他的硕士论文;他一直在找寻一种信仰,答案竟然在他的翻译中找到了。
那时在加州,他遇见了宣化上人,上人从中国北方来,迢迢来美弘扬大乘佛教。这些就读哈佛、哥伦比亚、柏克莱大学的研究生都愿亲近上人。时值越战方酣,这批聪颖的青年男女,有许多问题在他们的信仰中无法得到解答,极欲另寻安身立命之道。
上人和弟子们先在旧金山米逊区买下一栋老旧的工厂建筑物,改建成「金山圣寺」──成为往后洛杉矶、卡加利(加拿大)、亚伯达(加拿大)、马来西亚、澳洲、台湾等为数二十多所道场的发轫。
我在一九八五年才对佛教有了较多的认识,那时是上人邀请我来「万佛圣城」和恒实一起庆祝我六十一岁生日。
恒实受了具足戒之后,偕同另一位师兄弟,为了促进世界和平,一起沿着加州海岸公路,从洛杉矶「三步一拜──每走三步,伏地一拜」,到旧金山以北的万佛圣城,历时两年九个月,全程八百多英里。那段时间,加上往后三年,恒实都发愿禁语,唯有讲经说法才开口;以至我有五年没收过他的信,因为他的禁语亦包括了信函联络。
怀着很大的期待,我从俄亥俄飞往加州一游;有一义工居士开车来旧金山机场接我,一路将我载到圣城。
雷根主政加州前,这片占地广达四八八英亩,有七十五栋建物散置其中的园区,本是一所州立疗养院。之后新法颁布,明令禁止病人藉躬耕自食、自己维修器材来调养身心,结果,他们因被逼回原有的小房间而病情加剧,致使治疗加倍。由于医院需要雇用更多人手来料理院务,这变成州政府的一个沉重经济负担,导致它关门大吉。与此同时,州政府开始进行一项「在家看护」计画,即病人必须还归家中护理;计画实施结果,使得许多病人流浪街头,成为无家可归者,产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后来佛教徒买下这个园区,着手将它分辟成一座寺院、一所可容纳从幼稚园到十二年级的学校、一个老人安养之家、一所学院及翻译中心。追随老和尚的弟子,有一项首要任务:翻译佛教经典。这些梵文写就的佛经,早在佛教盛行之初,就已被翻译成中文;如今,这批有的甚至已得到梵文博士学位的僧尼,正努力和其他译经中心联手,将这些中文佛经再转译成十四种语文。
虽然我本人是忠实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,可是我也渴望尽量去了解那吸引我儿子全副身心兴趣,使他愿意为之奉献生命的宗教。恒实也曾是叶普渥斯城(爱荷华州)一名活跃的卫理公会教徒呢!
当汽车驶入翘著飞簷的万佛城山门时,我感觉自己好像正在走向一个陌生的国度;我知道我没法儿了解这儿所说和所做的,也不清楚人家会对我有什么样的期待。进了大门,车沿山丘上行,我可以看到高高的屋顶下有一尊铜铸大佛,旁边置有一口大铜钟。
我希望能再见到头一次来见到的那些僧尼。这些聪慧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尼师,也跟和尚一样誓愿独身;他们同样身着棕色衣袍,剃光头发。此时正是北加州的十一月,天候已然转冷,尼师虽然罩上深蓝色帽子,可是依然柔化不了他们脸上严肃的表情。起初,我对于女子竟可完全抛弃她的女性特质这一点,颇不以为然;可是当我开始理解她们之后,我已能超越朴实无华的外在,去理解这些肩负著使命,不再在意世俗表相的妇女。
我的女接待果悟,是一位越南籍的老菩萨,帮我「适应那儿的水土」。她领我去一间客寮安顿,以前是医院职员的居住区,现在改作客寮。每年皆有许多亚洲人来万佛圣城潜居静修,年长耆英则是专程来学佛的。
每天上午十一点,果悟居士带我上万佛殿;殿中僧尼分东西二序站列,在进日中一食之前,须先上供。宾客如有需要,亦可到斋堂另进早晚餐。
果悟给我一册内有中英文音译的课诵本,让我照着唸。当我们礼拜诸佛、从此佛名转到彼佛名时,法师都会敲一下磬。如果我在唸诵时没跟上,常有人轻柔地为我指出来。他们默默中给予的关照,令人好窝心。我发觉身为一名三步一拜行者的母亲,我受到的是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礼遇。
二十分钟的课诵完毕,我们尾随比丘们一路边诵佛号,一路朝斋堂走去。斋堂前方,上人端坐于正中平台,男女众分列两侧,左边约二十五位僧,和等数男宾,右边五十位尼师,及女宾亦约五十人。上人体型结实,著一袭黄色僧袍;他的相貌,截然不同与我所见过的任何人,他的表情流露着一种毫无矫饰,却充满睿智的慈悲。介绍认识之后,我闪过一种奇怪而悚然的感觉:他知道我在想什么!居士先供养上人,比丘和男众则列队到自助餐台取食,女众在后。
第一次用晚斋,我只认识一小部分菜肴,还有一些白菜、米饭,以及几盘用替代牛肉、鸡肉和其他肉类的豆腐制品所炒的一些我不认识的蔬菜。佛教的戒律禁止杀生,不止人,动物也包括其中,所以这些僧尼都是严格的素食者。果悟跟我解说每道菜的成分,还帮我筛选适合西方人口味的菜肴。对我胃口者取,不对者去;喜欢哪道菜,那道菜就有人帮我多上。我无菜不尝,免不了在盘子留下些剩菜。我本来还不知道这么做不对,直到果悟排队来到两个用来洗碗盘的水壶前,一个盛着浸泡餐具的清洁剂水,另一个装着用来冲洗的清水。我按部就班前,有人得来帮我清理我盘中的残肴;那当儿我明白了,显然,佛教徒不浪费食物的。
我们在静默中用餐,这使我发现:它能令我集中心思在食物上。佛教徒不仅食儿品其味,更念及食物「粒粒皆辛苦」。他们省思:自己何德何能,得以享受这些食物,以及贪欲如何毒害心灵;他们视食物为疗饥的药石,他们受此食以助修道,来利益众生。
有一天斋毕,上人开始用中文开示,一位尼师英译。上人说:「恒实的母亲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庆祝她的生日。」一尼师当即为我端来一个素糕;没想到上人也留意我们西方的习俗了,我更肯定他会入境随俗地接受美国风俗。
往后的开示,使我深受感动。一名美国尼师、一名亚洲宾客和我三个人应邀各自谈谈我们的儿子。尼师出家前有个儿子,我和那位马来西亚来的母亲,则同样有个出家为僧的儿子;尽管我们的年龄和文化背景有别,但我们那份爱儿之心和失落之感却无二致。
马来籍母亲和我都担心:这个带走我们儿子的宗教,可会浇熄他们年轻人的满腔热忱?我虽然一点都不怀疑恒实的诚心,可是在那样一个外道充斥的时代,我们做母亲的难免会质疑上人的出发点在于利他。如今,住在佛寺的这几天,使我发觉:我对法界佛教总会的种种不信任和疑虑,其实都是自己惹出来的,都与实际不符。认识上人后,我更知道自己错估了他的用心,以及恒实的见识。我同意尼师的那句话:「现在啊,该换你跟儿子学习了!」
当上人问我有什么要对大家说的时候,我借机为所有僧尼的母亲嘱咐他们:「当你们义无反顾地追求你们的新生活时,别忘了你们在家的父母,他们也想分享你们的经验,一如他们曾分享你们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那样!」我希望我那「写信给妈妈」的叮咛,能入其耳、贯其心。
当上人结束今天的说话时,午斋也就随之结束了。我们再度排班回到大殿三皈回向。我们行头手接足礼,拜佛多次。饱餐之后,能够运动运动,还真不错!
一位基督教牧师请宣化上人解说拜佛的好处,他这么回答:「拜佛有如宣誓效忠国旗。国旗是…一块布片,而代表国家。身为公民,你用宣誓效忠,表达尊敬及认同你的公民身分。」
「在佛龛上的这尊佛像绝对不是神,也不是圣人。这只是一种表法,用一种艺术化的形象,来显示过去某位已经证得无上智慧的人;佛因为修行自性,而达到觉悟的境界。这尊像,是象征他已充分发掘人性的潜能,及他对至善与大悲的追求。当你礼佛时,象征性地,你是在礼拜你自己本来具足大智慧的潜能。再说,礼佛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,绝非迷信或消极的偶像崇拜;拜佛是一种对真理的修持,是积极而主动的。」
为示庆生,及我的来访,一天,出家众们安排了一个放生仪式。信徒们先在旧金山买下一些将入餐馆油锅沸汤的生龟,装入木箱,运回圣城,摆在大殿待放。佛像前,木箱里的乌龟疯也似地不停抓呀爬呀;可是当磬声一起,大众开始唱诵,乌龟就变得安静下来了,好像这些声音能够抚慰牠们似的。大众诵《放生仪规》回向给牠们,因为佛教徒相信放其生路,这些乌龟能继续修到一种比较高等的生命,而免于无止尽的生死循环。
仪式完毕,果悟驾车带我到附近的湖准备放生。以前我经手的乌龟,没有一个大过一块钱银币的,可是现在每只都有餐盘那么大,说好每人放一只。我挑了一只看起来还算温驯的,一抓起牠身躯的中段,牠那小小的四肢就变成了四个旋转不已的转轴,我得当心别让牠勾住我的衣裤。牠渴望入水了,所以我必须快快将牠放下。当我把牠一放入水中,见牠立刻消失在混浊的湖水时,我以为放生已经结束了。
果悟说:「看哪,牠们在谢我们呢!」我原以为她在开玩笑,但就在离岸约莫五十呎远的湖中,冒出了一些小头,是乌龟在转头回望我们,然后,再度消失。果悟说:「继续看啊!」
一两分钟之后,乌龟的头又浮现在湖面更远处,转过头,回顾我们。我真不敢相信。
果悟说:「牠们会谢三次。」确实如此。
这些事我无法解释,但知道事情确实这么发生过。往后,只要我一看到菜单上写着「乌龟汤」,就会想起那次称心的善行。
到圣城住了三天,我讶异地察觉到:自己对往日穿戴的服饰,不再那么感兴趣了。我的确喜欢色彩与式样,但在这样宁静的地方,他们已没像以前那么重要了。这是头一回,我对棕色朴素的僧袍有了好感。归去前,再度与上人透过翻译一谈,也多了一层对佛教的了解。
他告诉我:「你们的上帝是个有嫉妒心的上帝,他说:『除了我,你们不能再有其他的上帝。』佛说你可以一面信你的上帝,一面也信佛。你的上帝于你有如家长,你是他的孩子;如果你犯错,得要他原谅你。佛和你,就像大人对大人式的对等关系;你做啥坏事,你得自己负责。」
佛教徒的慈悲和善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,他们过著一种令我敬慕的宗教生活方式。
恒实已经找到一种既充实又有益的生活方式。去年,他获得加大柏克莱分校的佛学博士学位,目前正掌理柏克莱佛寺,并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任教。他是「开创宗教联合会」的理事之一;也是佛教书刊的作者,并在柏克莱「神学研究院」讲授孔子学说和佛教教义。他到美国和亚洲国家四处演讲。
我知道他绝不会结婚而让我抱孙子了,这点虽然令人遗憾;可是他所影响的孩子,远比他当上一个父亲所能影响的孩子,要多得多。这使他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快乐!说句心里话,我为我儿子是一位佛教徒而自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