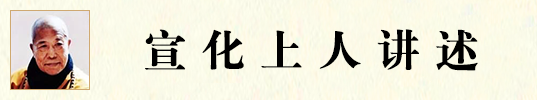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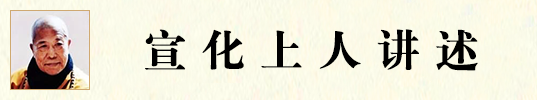
上人在一九六二年,应香港一些徒众之请,来到美国三藩市中国城设立了佛教讲堂。一九六三年,因当地徒众对法不恭敬的缘故,上人离开了中国城,搬到日本城附近一座破旧的维多利亚式楼房的第一层楼,楼房中其他房间的住客,则为年老贫穷的黑人,和一些到处寻求人生真义的年轻美国人。所有房客共用一间厨房。
我第一次遇见上人,是在一九六六年,那时我是个穷学生,正在找寻住处,所以我住进了二楼的一间房。当时楼中的年轻住客在下意识中,都感觉得到这位法师是一位不平常的人物。但是因为我们对佛教是一无所知,所以也弄不清楚他是怎么回事。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中国佛教的和尚,但也不懂佛教和尚是干什么的。当时有一位年轻人,甚至皈依了他,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皈依是什么意思,是不是和出家有什么分别,也不知道。我们对一些最基本的佛教仪轨,及供养三宝,或持戒,则压根儿一点概念都没有,上人自己也从未告诉过人他是祖师,在中国和香港还有成千上万的皈依弟子。
当时三藩市许多中国人对上人十分不谅解,因为他搬离了中国城,只有少少几个最忠实的弟子,还定期来拜见上人,并带来些供养。上人在收到这些供养之后,也总是拿来与其他住客共享。有时他会放几包米在公用厨房供大家食用,所以我们不至于挨饿。在佛教假日时,或当上人有多余的食物时,他也会请我们一起吃中饭,上人并且自己掌厨,做出来的饭菜还蛮好吃的。
那时,即时只有两三个连中文都不懂的人来听法,上人也以后来对千百人说法时一样的态度说法。我记得我去听上人讲解《法华经》时,上人即以我们现在所习知的庄重肃穆的态度解说。上人坐在二张摺叠式的野餐桌前,背后是一面陈旧的黑板,通常没人翻译,有的话也只是两个年轻的中学生,翻得也不太高明。我那时对经文毫不了解,我去听讲时,只是想和上人在一起,听听他的声音。
上人那时每晚七时至八时,与大家共同坐禅,这是当时有的年轻人最欢喜的活动。通常会有一些人来参加坐禅,我自己在那儿住久了,也渐渐常和上人一起坐禅。虽然当时附近有一所知名的参禅中心,但我却觉得因有上人在座,我坐禅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。
大概过了半年的光景,我才认清楚了上人,认清楚了之后,我十分惊异。虽然那时我对佛教仍然是一无所知,但是我却意识到上人和我一生中所碰到的人,完全不一样。我发觉上人是完完全全没有自己,一丝一毫的自我都没有,在上人身上,一点利害冲突都找不出。他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还更深,他包容我的程度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,而且很慈悲地关怀我。所以在上人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。我也感觉到上人有很深的智慧和神通,但在日常生活中,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,一点也不起眼,这种认知并不是我一人独有的。当时认识他的人,不论他们的种族、教育背景是什么,都有这种感觉,或者更深也可能。
几个月之后,我满怀兴奋地到亚洲──佛法的老家去找寻佛法,也是我的无知,让我碰上这样的奇遇。我在亚洲碰到的,只是传统佛教机构,二千五百年陈旧的外壳,除了少数几个例外,其他的地方完全都没有活的气息。
我回美国之后,即在大学佛学学术上追求。我先进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硕士班,后又进入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博士班,我学校中顾问们,对佛教义理知识的广博多闻,使我叹为观止,但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让佛教进入他们的私生活领域中,还抗拒得这么厉害。那几年这双重失望,引起我很大的痛苦。对于我,或者需要有这样的教训,使我在遇到一位真正的大师之后,才懂得他的宝贵,才会珍惜他。
对我来说,能以常在一位像上人这样无我的人身边就够了,但是上人与我和我的家人关系十分深切。上人不只救了我们,还有其他许多人的性命。上人在我们遭遇危机时,帮助我们,给我们的孩子们解决问题。对于上人赋予我们的,我们的感激之情,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。
更有价值的是,上人对我的生命带来了最究竟的意义。日常生活中,他的一言一行,在在都在阐说佛经中演说的佛法,不是幻想、神话,或抽象的戏论,他让我知道佛经中所说的法,都是活生生的、真实的,而且在我们生活中是可行的,是切合实际的。我记得上人曾说:“我们讲经时,要拿这部经当做是自己所说出来的,与我们合为一体,不要将自己和佛经疏远了。”上人一生以身作则来示范这一点。
“接受”的时期结束了,现在是自己站起来的时候了,在法中做个成人。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,这对我还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,不要因为我们对上人的亏欠太多而沮丧不安,因为这笔债太大了,我虽知识有限,也知道我们永远也还不清的。上人常说“尽力而为”,现在我只能以我有限的知见,尽我有限的能力,在我自身,也在这个无常多苦的世界上,来继续上人的工作。上人虽然离开了他的肉身,但是我知道上人还在我心深处,在这一处真正的净土里,无内亦无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