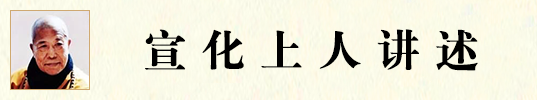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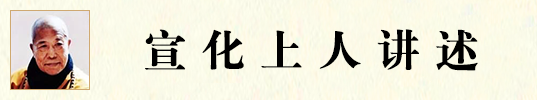
今天我有一点高兴,又有一点悲伤。高兴的是能与诸位大善知识在一起;悲伤的是因为以前我也来万佛城与金山寺,常常被叫上来讲讲我所了解的佛法。那时下面总是坐着一个人,有时他一句话也不讲,只耐心地听我讲;也有时他改正我,有时他也替我补充一些。今天我坐在这里,可是那个人不在了,他永远不会再来那样改正我、教导我了!在人的一生中,能找到一位可以改正你错误的人,机会是非常难得的。今天我失去的正是这么一个人,那人就是我的师父,也是各位的师父。
我不像各位住在万佛城、金山寺的人那么幸运,常常在师父身边,能够常听师父的教诲。因为我业障很深,还必须在社会上为生活挣扎,不能来万佛城亲近师父。也正因为这原因,所以师父所告诉我的几句话,我把它看做是宝贝一样。因为太少了、太稀有了,所以我就尽力把这很少的几句话,看看如何能运用在生活上。因为师父给我的话很少,所以我非常珍惜。
一九七七年四月,我去加拿大开会,并发表一篇“力学”的文章。会期一周,文章报告完毕,我就去金山寺见师父。一见之下,我就感觉非常亲切,当时金山寺在十五街,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地方自己来过。在那之前,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尚,也从来没有进过佛教寺庙,所以那次是我第一次接触佛教,第一次见到和尚──就是上人。我十二岁离家,为生活奔波,非常艰苦。十二岁起就没有再向谁叩头,连想也没有想过要给人叩头。我和上人一见面,就有说不出的亲切与自在,好像回到家一样。各位或许都有温暖的家庭,无法体会,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那感受,于是我立刻给他叩头了。师父一边笑,一边说:“教授向我叩头!”
叩下去站起来,我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刚强、不容易屈服的人。我就想我怎么给这个和尚叩头呢?那个感觉说不出,就觉得自己好像变了,一个突变。我很开心,就皈依他。当天晚上,做完晚课后,十点多钟大家都睡觉了,我坐在佛堂凳子上,脑子没有想什么,觉得空空的,说不出任何感觉,那种发呆的样子。坐在那里,师父就来了,我也没有跟他讲话,他也没有跟我讲话,就坐在我的身边。我们并坐了十几分钟没有说话,然后他突然大声说:“断欲!”当时我没有害怕,也没有动一下,但是断欲的印象,就像狮子吼在我心里非常深刻,不会忘记!因为我认识佛教是从《六祖坛经》,经中并没有提到断欲啊?它说:“淫心本是净心因。”那次,“断欲”在我脑海里非常深刻。“欲”确实是我的大病,可是我并不觉得,从那天开始我知道自己有一个病。我回去就开始实行,这么多年了,但是我时时在努力,非常艰苦,它影响到我和我的家庭。后来才知道断欲是经典中佛陀最基本的教诲,这是师父第一次的教化。
次年,一九七八年,我随师父到南洋去,共有六个礼拜。这是我接近师父最长久、听他教化最多的一段时间。在这里只举一件事,我们到一间南传庙,住持是一位在马来西亚政府很有影响力的 Dham-mananda法师(达摩难陀)。到他的庙上,师父和这位法师坐在中央,我们九个人就围着师父坐,我和师父座下两位法师闭着眼睛在打坐。这位 Dham-mananda法师的一位在家徒弟,他的大护法,是一位教授,他就起来质问师父:为什么大乘法师不礼拜小乘法师,不尊重他们?他还说了很多,我不记得了。师父没有回答他,他还继续说着。我正在打坐,没有听他讲话,不知道他讲什么,也不知道为什么,就站起来了,在他面前给他叩头。然后我问他:“请问你,我在叩头前是大乘,还是小乘?我在叩头后是小乘,还是大乘?”他有点呆了,不能回答我。于是乎他的问题就解决了,他不再问了。同时在旁边有一位黄姓居士,他是师父到南洋的请法者。黄居士对他说:“他也是一位教授。”从那时开始,他就对我非常好,也不再问师父问题了。
那次旅程中,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开个小小的会议,师父高坐,我们坐在地板上,检讨一下前一天的工作。那天师父坐好了,就从椅子上挪下来,坐在地板上我身边,他说:“昨天你做得真是太好了!”我说:“师父您不要夸奖我,好不好?谁夸奖我,我都不怕,因为我不执着,我不需要。不过您夸奖我,我有点受不了,我会执着,因为我太高兴了!”师父说:“哎!我不是夸奖你,我是说真话啊!”这比夸奖还厉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