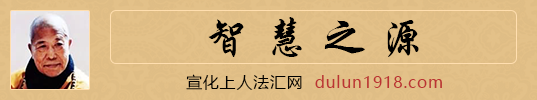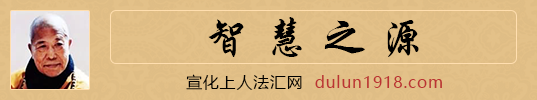◎比丘恒顺法师讲于二○一四年五月十四日万佛城大殿
我在男校高年级教一堂佛学课,我经常告诉学生的一个观念是:佛陀的教化是独特超凡的,他的教义和其他宗教截然不同。佛教的观念是,不管我们有多坏、做了多大的恶事,都可以弥补。即使是魔王波旬——宇宙里面最坏的个体——都还是可以改变而成佛。没有任何众生是命中注定无可救药,或是永远沉溺于生死轮回中。每个众生,不管是谁,都有变好的潜能而究竟成佛,而这个潜在的能力是永远跟随着我们。这个道理真的很神奇,也很不可思议。
最显著的一个例子,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弟子的前生故事。每一位佛都有两位大弟子,一位是神通第一,另一位是智慧第一;以释迦牟尼佛来说,舍利弗是智慧第一,目犍连是神通第一。有一部经典描述目犍连尊者在无量劫以前,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魔王波旬。虽然过去生中曾经是魔王,但是他赎去前生的恶业,成为佛陀忠心的大弟子,而且是神通第一。这实在是最佳的写照,即使最顽劣的众生也能够返迷归觉,不仅成为佛陀神通第一的弟子,在《法华经》里目犍连尊者也得到佛的授记,当得成佛,佛号「多摩罗跋栴檀香如来」。
接下来,谈谈我个人对忏悔法门的体悟,不过先要描述一下我的背景。一九七四年我在泰国当沙弥的时候,读到了关于上人的事蹟,于是决定到金山寺,依止上人座下修行。本来我是打算在曼谷的巴婆尼瓦斯寺修行几年,然后到泰北(乌东省的帕邦塔寺)当一辈子的森林比丘。我的目标是希望在阿姜摩诃布瓦(阿姜曼尊者的著名弟子之一)的指导下,得到开悟证果。但是读了上人事蹟之后,我改变计划回到美国跟随上人,因为我心里很确定,上人是我寻找已久的心灵导师。
一九七四年,我来到了金山寺。因为以前是学小乘(南传佛教),所以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,只待一个星期就跑回芝加哥。几个月后,大约是八月初,我又回到金山寺参加第二届六周的暑假班(一九七四年八月三日到九月十四日)。暑假班一开始先打一个禅七(八月五日到八月十二日),每天早上三点到半夜。当时的我,连散盘都撑不到三十分钟,更不用提单盘或双盘;我是练习了三年才有办法双盘,而且也只能坐五分钟。不管怎样,那个星期还是咬著牙撑过去;从那次以后,我就留下来了。
第一次接触忏悔法门是一九七四年在金山寺,当时每个礼拜六拜〈大悲忏〉,是用中文唱的,每个月拜一次〈药师忏〉,是用英文唱的。有些出家人发心翻译〈药师忏〉的忏文,调子也是他们自己编的,很好听。〈大悲忏〉和〈药师忏〉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忏悔法会。
刚到金山寺,我一直无法适应道场的作息,是后来的两件事情帮我度过这个难关。第一件事是发生在禅七的时候。因为太严格了,所以到禅七的第五天我实在受不了,想打包走人;直到第六天,上人对「四圣谛」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开示。正如前面说的,我一直都是学习南传佛教,而且准备在泰国的森林寺庙过一辈子,因此还是非常执著南传的教理,对于大乘佛法「众生皆堪作佛」的道理,我实在无法想像它的可能性。然而上人对「四圣谛」的解释,却是我听过的开示中讲的最好的;也因为这个开示,让我有很好的理由说服自己留下来。虽然如此,金山寺紧凑的作息,我依然无法适应。
在讲第二件事情之前,要先描述一下当时金山寺的生活。最早的金山寺在三藩市的十五街,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。佛殿在一楼,大约是一百二十呎长、三十呎宽、二十多呎高。现在圣城这尊千手观音,当时还没贴金,高度几乎要碰到佛殿的天花板。佛殿旁边是厨房和斋堂,面积加起来跟佛殿差不多。
从早上四点钟的早课做完,一直到晚上九点半,整天都不会有时间回到三楼的寮房。大部份时间我们都在佛殿或者斋堂,工作、读书或是打坐;换句话说,不管你做什么,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,没有所谓的私人空间。晚课做完,九点半上楼休息,隔天早上三点半起床准备做早课。对我来说,这样的生活真的很难适应。
再描述得详细一点,早课差不多五十分钟到一小时,然后休息十到十五分钟。五点十分,开始打坐一小时,然后行香二十分钟,接着再坐一个钟头;打坐完之后,就是出坡时间,每个人都有分配的工作;十点四十分上供(跟现在不太一样,现在是十点半),然后用斋;结斋之后,又继续工作。现在万佛城是每天下午一点钟拜〈大悲忏〉,那时只有星期六才拜〈大悲忏〉。
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,有时候是五点四十分到六点四十分,是打坐时间。七点做晚课,现在圣城是六点半做晚课。一个小时的晚课之后,上人就讲解《华严经》,包括弟子英文翻译总共一小时;上人大约每讲十分钟,就会停下来让弟子翻译成英文。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刚到的时候,上人正在讲第三品〈普贤三昧品〉;听经结束后是拜〈万佛宝忏〉;在我来之前,他们已经拜了好几年。 每天晚上拜一点,拜到九点半,也结束一天的功课。
禅七之后,虽然还是很挣扎,但我还是继续参加暑假班。对于大乘的「众生皆可成佛」的理论,有好一段时间我无法接受。不过,参加一个礼拜一次的大悲忏法会,让我觉得自己的业障越来越少。虽然〈大悲忏〉里面描述的某些道理,譬如「我与众生,无始来今,广造众恶」,我并不是很了解,但是它真的有效果,每次拜我都可以感觉自己的业障一点一点地销融。我不是记得很清楚,大概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,我觉得自己终于过关了,可以安住在道场,毫无疑悔地终身修习大乘佛法。〈大悲忏〉的确有大威神力,能让人脱胎换骨。那时好几位一起拜忏的同参,也有同样的感觉,这是修行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。因此,帮助我留下来的第二件事,就是拜〈大悲忏〉。
在这个始料未及的转变没多久,我就剃度为沙弥,距离我八月份刚来,大约是一年的时间。几个月之后,大概是一九七六年三、四月,上人宣布我们要开始受训,以准备成为比丘、比丘尼;当时男众大约有七、八个人,女众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。由于正值金山寺的防震补强工程,我们每天都要作六、七个钟头的工。那具足戒的课程呢?就是作工、拜忏。所以每天早上的功课做完,八点钟开始,拜一个半钟头,和我们现在早上五点到六点拜愿的形式一样;晚课之前,再拜一个半钟头。这就是我们受戒的「基础训练」。师父有交代,要诚心地忏悔自己做错的事,和不好的习气毛病。当然,我们都依照上人的话去做。
如果没记错,这就是每天做的功课与工作,没有其他特别安排的课程。不过我们都有自己的功课,譬如背《毗尼日用》五十三小咒,还有莲池大师节录的《沙弥律仪要略》,下篇的威仪门虽然也要读,但不要求背起来。我们大概准备了一年的时间,隔年(一九七六年八月)我们就都受了具足戒。
尽管当时受戒没有像现在上很多的课,但是每天晚上师父都会讲解《华严经》,连英文翻译在内一共一个小时。不管你是亲自听过上人开示,或是听过上人开示的录音带,都会有一种感觉,就是好像他是针对你讲的,实在很不可思议。那时候,师父常常就坐在前面为我们说法,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;神奇的是,他往往都会讲到我们心里的问题、需求或者愿望,而这些正好都是我们想知道的事。
接下来是我对忏悔法门的经历和感想。前面有提到当年金山寺里举行的各种拜忏法会,在刚出家做沙弥的时候,除了这些法会,我听说有些师兄弟修过一种特别的忏悔法门,令我很感动,那就是拜《华严经》。虽然是拜经,事实上也是一种拜忏,因为一字一拜,拜下去的时候唸〈忏悔文〉:
往昔所造诸恶业,皆由无始贪瞋痴;
从身语意之所生,一切我今皆忏悔。
这段忏悔文是出自《华严经》最后一卷〈普贤菩萨行愿品〉。于是我对大众发愿,也要一字一拜《华严经》,每天早晚各拜一个钟头,这样持续了六年。大概是受具足戒之前的半年,上人让我在金山寺的办公室当恒观的助手,恒观当时是金山寺的当家。我很少和上人直接讲话,因为福德不够,也不太会讲中文,所以都要透过恒观。
从我一九七四年刚到金山寺,一直到八零年中期,恒观是我们大家钦慕而且尊敬的一位美国比丘。虽然有点脾气,但是他非常能干而且诚心;最重要的一点,他对师父非常忠心。当他助手的期间,我得以能够积功累德,同时也学会一些中文。
一九七七年,在恒实法师他们开始三步一拜的几个月后,有一天上人对大家宣布,要改在万佛圣城讲《华严经》;也就是说,在金山寺这边就不讲《华严经》了。现在我们每个礼拜三听的〈十地品〉,上人是从一九七七年二月讲到七月,在金山寺讲的,偶而几次在万佛城。而从一九七七年十月开始,上人就完全改在万佛城讲《华严经》了。在宣布这件事之前不久,师父突然问我可不可以当金山寺每日课诵的专任维那,因为本来是比丘和沙弥轮流,一个人轮一星期,因此这算是一个蛮大的改变。上人虽然是我们的师父,我们也视他如父亲般的敬仰,但他从来不会命令我们去做任何一件事;他总是会询问我们的意愿,确定我们同意照他建议的去做,而不是被强迫的。
那时候大部份的出家人都已经搬来万佛城,只剩下几个比丘还留在金山寺,甚至有些尼众和女居士更早就先搬来了。当大家都搬到万佛城之后,上人就只在圣城讲《华严经》。上人每个礼拜有三天住在圣城,星期五来,住到星期一早上离开,其他四天在金山寺。这就是一九七七年底开始上人每周大致的行程,恒观负责开车接送,我则一直待在金山寺。
虽然不在金山寺讲《华严经》,但是上人还是有其他开示,他会讲《佛祖道影》,也跟我们讲叙述历史人物的《水镜回天录》。所以我听过的印度历代祖师和中国禅宗历代祖师事蹟,加起来大概有三百多回,还有《水镜回天录》的讲解至少也有一百多回。
大约一九七七年底或是七八年初,有一天恒观跟我说:「师父要我告诉你,从现在开始,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找他,不用再经过我。」我们平常都在一楼的办公室,而师父通常是在三楼他住的地方。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师父,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
搬来圣城之后几年,上人就教大家每年要拜一次万佛宝忏,第一次举行就是一九八三年。当然,住在金山寺的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参加。令人遗憾的是,恒观一九八五年还俗,那是个莫大的转变,因为当时我们帮师父处理许多事情,譬如签证、不动产、税务、信件等等,佛教总会的行政管理中心就设在金山寺,所以当他离开以后,我的工作和责任增加很多。面对这样的情况,上人怎么做呢?上人非常善巧地给我一个方便法门,他对我说:「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要做,所以从现在开始,晚课还是对外开放,但是晚课以后的开示我们先暂停,让你有较多的时间去处理公务。」师父就让我这样子做了半年多。
这里顺带提一件事,可以当作历史资料。师父是在下午讲《佛祖道影》和《水镜回天录》,晚上就是恒观和我轮流翻译师父讲经的录音带,就像现在万佛城晚上听经这样,不过当时我们只翻译上人讲的,没有结法缘,时间是八点到九点,一个小时,不是一个半小时。现在金山寺还保留着上人一九六八年讲《楞严经》的磁带,大约有二十二到二十四卷,还有一九六九年讲《华严经‧普贤行愿品》的磁带,也是很多卷。这些磁带的体积不小(直径约八英吋),听的时候是用一部老旧的录音机来听。我们先听录音,然后再翻译成英文。整部《楞严经》听完、翻译完了,就改听〈普贤行愿品〉,也是先听后翻;听完了,就又换听《楞严经》,两部经互相轮流着。我记得《楞严经》听完差不多要一年,〈普贤行愿品〉大概要四个月,所以从一九七七年底到一九八五年,两部经来来回回大约听了六、七次。那时候如果上人在金山寺,下午我们就可以听他讲《佛祖道影》或《水镜回天录》,晚上就听他讲经的录音带。
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金山寺,可是却一直很想有机会能在万佛城对四众忏悔,因为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八年之间,我做了许多不对的事。师父很慈悲,让我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三十日那天当众忏悔。不可讳言,在几百个人面前说出自己错误和愚痴的作为,是一件很困难而且很尴尬的事。师父让我在他晚间讲经结束之后对众忏悔,并且在我忏悔完后讲了一段很难忘的开示。有时在斋堂吃饭我都还会听到这段开示的片段,所以我要把其中一些重要的内容跟大家分享。我很幸运有机会能听上人的开示数千次,《华严经》大概就一千两百次,在金山寺跟万佛城的开示加起来也有一千次。然而这段开示,是所有开示中最令我感动的。师父在里面有特别提到,这些话不是单单为我而说的,是对所有万佛城的比丘、比丘尼和在家人说的。这段开示总共有四个部分。在开示的最后,上人对我说:「你知道,你造了很多的恶业,做了许多不对的事,你应该留下来拜万佛忏,忏除你的业障,你就留在万佛城吧!」
跟随师父十四年,我一直都住在金山寺;现在师父叫我住在万佛城,拜万佛忏,而且他叫我要「拜全程」。我刚说了,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,所以万佛城已经是第六年举行万佛忏,但却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法会。对我来说,这是个非常奇妙的过程。
拜忏开始了几天,有一天上人到佛殿来,大概是下午第一枝香的时候。当时大家都正在拜忏,上人用手势叫我跟他到佛殿旁边,他用中文对我说:「有一个罗刹鬼要你的命。如果你再搞砸,你就完了!」讲完之后,我回到佛殿继续拜,而且非常认真诚心地拜。事实上,从那次公开忏悔之后,我就很积极地想在修行上用功夫;现在上人又说有个罗刹鬼要我的命,这话让我更卯足劲地用功!那一次我在万佛城住了八个月,之后师父就让我回金山寺。
现在是上人当时开示的第一个部分。不过要先提一下,上人虽然看起来很严肃,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慈悲的人。几个星期以前,我听到有人讲上人的故事,他把上人描述得好像很严苛的样子;在我服侍上人的十五、六年间,我从来都没有那种感觉。当然每一个人跟师父相处的经验不尽相同,然而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,上人都是很慈悲的。不可否认,有些人需要「严厉的关怀」;即便如此,上人也完全是出于慈悲,以当事人的利益为出发点,第一部分的开示正是展现这个精神。
开示是这样说的:
各位善知识,做人要「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」。你一定要改过,如果你知道你做的事情不对,还继续做,那你决定会堕到地狱去,这是没有情面可言的。
尤其是出家人,如果你尽打妄想,不管你觉不觉得羞耻,只要还有这种不干净的妄想,你一定会下地狱的。不是佛菩萨把你送到那里去,是你把自己送进去的。
但是,如果你可以改过自新,那么「弥天大罪,一忏便消」。人不要怕犯错,最怕有错不改。万佛忏现在就要开始了,你造了那么多的罪业,你要发大忏悔,好好痛改前非,好好地在万佛前忏悔,千万不可以懒惰懈怠。
如果你可以这样做,可以改过,那你还有希望。不管谁有错,如果可以改就有希望,但是要真的改才算!